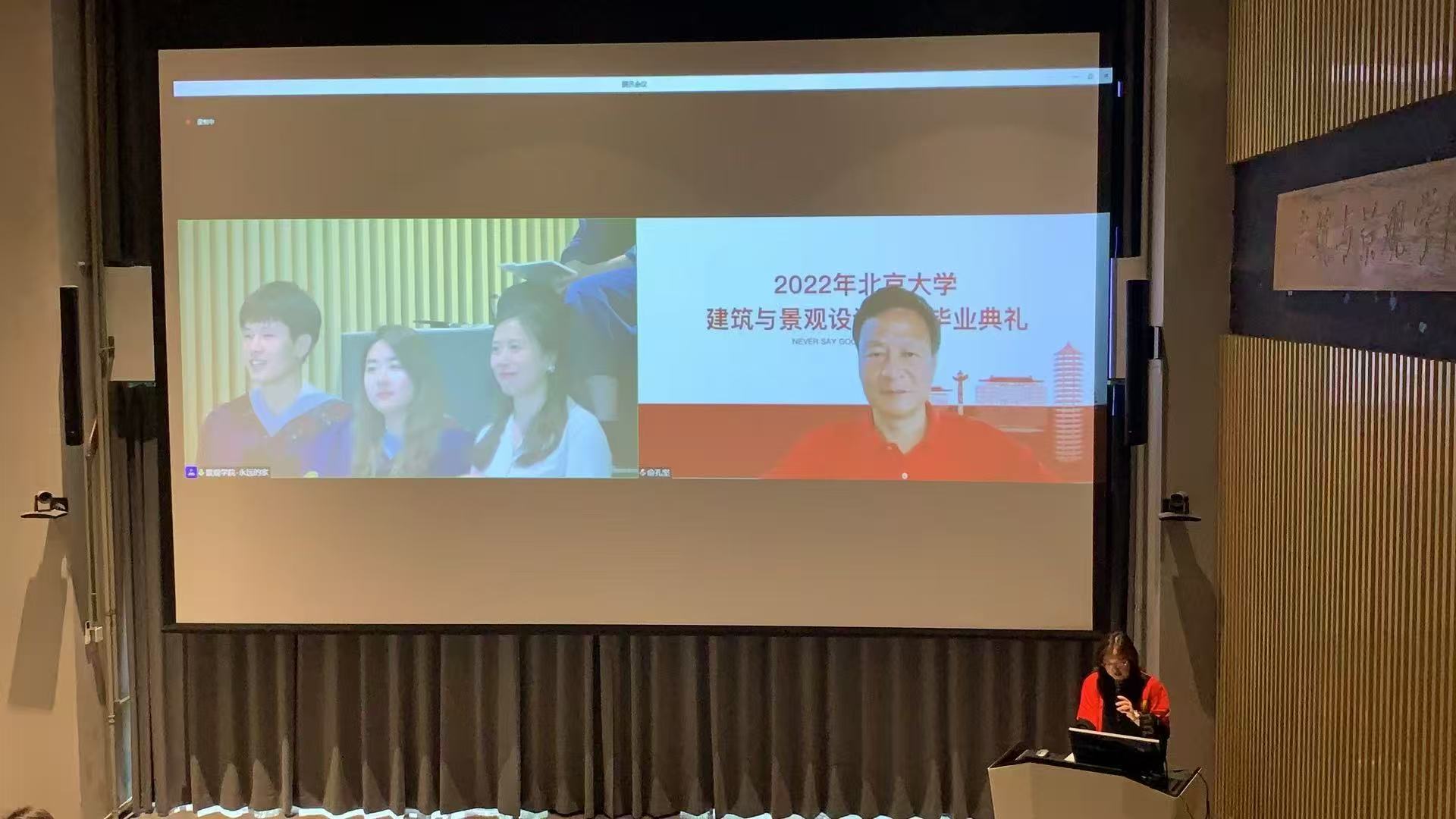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天,有很多话想说,却悲伤难抑、思绪如麻。我们不敢相信,也不愿相信。俞老师的理论及作品是我选择北大景观的最大理由,聚在这里的人有着相同的理想——“再造秀美河山”。见过俞老师在讲座上的笃定自信,见过他在土人批改方案时的雷厉风行,见过他在课堂上的慈爱温暖。他就像是一轮耀眼的太阳,现在化作星辰,也值得我们永远抬头仰望。
2021年的乡村设计课堂上,他带着我们穿梭在西溪南的田间地头,指导我们小组深入研究农业源面污染治理,最后的研究成果也有幸汇集为《海绵田园》一书出版。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我们的研究发现,而是俞老师在课程伊始讲座上的几句话:“什么样的乡村可以发展以旅游为主的乡村振兴?一是便于到达的时间距离,二是优美的自然生态,三是丰富的历史文化。”他的话就像是一道闪电使我顿悟,盲目大力发展乡村旅游、全域旅游等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毕业之后,我进入体制内,在评审方案时发现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政策资金,将完全不需要“海绵城市”建设的工业园环境提升项目硬套上“海绵城市”的壳子。先进的理念被曲解被误用,难道这就是“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”吗?我感到心痛而又无奈时想起了俞老师的笑容和声音。他从来都没有被争议和诽谤所打倒,数年如一日地坚持探索着自己的理想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秒。
斯人已逝,生者如斯,这星火永不灭。